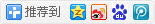货车撞过来的那一刻,亓莞陶听到了刺耳的鸣笛声,白光闪过,身体被重重甩到地上。头脑一阵嗡鸣,痛感达到了极点竟有些麻木,只有血液的流失最为清晰,亓莞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——我要死了啊。 手上拿着的袋子甩落在一旁,里面装着的是送给祁鹤的安全套,祁鹤跟他炮友用的。 还没有提醒他,那个炮友看着有点怪,一副身体被掏空的肾虚样子,做之前最好做个体检。 亓莞陶的意识越来越模糊,有那么一瞬间,他觉得自己贱的要死。 亓莞陶是个孤儿,六岁时被祁母收养,祁鹤比他小两岁,小时候还有些
每日推荐:
段嘉衍和路星辞全文阅读有 ,
天降萌宝霍总请签收漫画讲解 ,
怂A当然要亲完就跑 邺北 ,
IPHONEXSMAX欧美高级 ,
全职名医TXT免费下载 ,
剑域风云小说在线阅读 ,
心有不甘之苏寅正重生 ,
四合院知青下乡融合 ,
烽火战国官网手机版 ,
陈扬绝世高手最新免费全文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