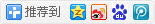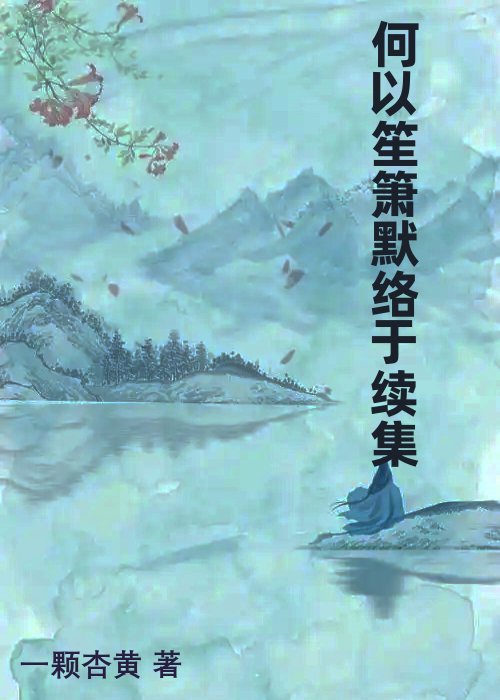挂了电话,杨树林腿有些发软,他半撑着坐在桌子上,突然觉得浑身有种无力感。 他其实没怎么变,跟以前一样是个懦弱又不敢反抗的怂逼。 他这么在心里边贬低着自己,边低声骂了句“妈的”。 按照蒋净明的安排,杨树林坐上了去聚会的车。 但他连聚会在哪儿举行、有什么人都不知道。 车子往偏僻的郊外开去,杨树林坐直了身子,问司机:“还没到吗?” 司机头也没回:“快到了,杨总。” 话虽这么说,可直到过了半个小时,汽车才绕过弯弯曲折的小路,慢
每日推荐:
段嘉衍和路星辞全文阅读有 ,
天降萌宝霍总请签收漫画讲解 ,
怂A当然要亲完就跑 邺北 ,
IPHONEXSMAX欧美高级 ,
全职名医TXT免费下载 ,
剑域风云小说在线阅读 ,
心有不甘之苏寅正重生 ,
四合院知青下乡融合 ,
烽火战国官网手机版 ,
陈扬绝世高手最新免费全文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