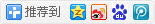周末,陆沿瓷值完夜班,从早上八点一觉睡到了下午。 闹钟一响,他翻了个身从床上滚下来,用这种方式强制自己起床。 这是他从初中就开始采取的办法,陆沿瓷自认自己不是个自律的人,好在他对自己要求高,于是总会发掘出一些奇奇怪怪的,能让自己生活规律起来的小技巧。 他从地上爬起来,此时再怎么困也该被摔清醒了。陆沿瓷走到浴室洗漱,男人眼下晕着乌青,按理来说应该是憔悴的,但因为那张脸足够好看,这点痕迹便成了一种修饰性的病弱美。 镜子里的人额前四六分刘海与眉平齐,冷峻的眉间有
每日推荐:
段嘉衍和路星辞全文阅读有 ,
天降萌宝霍总请签收漫画讲解 ,
怂A当然要亲完就跑 邺北 ,
IPHONEXSMAX欧美高级 ,
全职名医TXT免费下载 ,
剑域风云小说在线阅读 ,
心有不甘之苏寅正重生 ,
四合院知青下乡融合 ,
烽火战国官网手机版 ,
陈扬绝世高手最新免费全文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