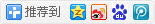等季弦嗓子喊的有些哑,甚至只能可怜地呜咽几声的时候,晟煦终于有了动作。 她将方才那陆陆续续接着水作背景音的紫砂壶拎起来,慈悲地说:“也不知道你是谁家的狗,叫的嗓子都哑了。可惜我毕竟是人,听不懂狗叫。可怜的贱狗。喏,赏你点水喝吧。” 季弦顿时觉得天要塌了。 他忍着晟煦的戏弄,认了贱狗的名号,还尊严尽失地COS了这么久,结果一切都是一场玩笑。 他自暴自弃地想,还不如索性释放出来,哪怕一时难堪,也好过被这样取笑。 若还要再饮一壶,尿包一定会爆炸的。 &n
每日推荐:
段嘉衍和路星辞全文阅读有 ,
天降萌宝霍总请签收漫画讲解 ,
怂A当然要亲完就跑 邺北 ,
IPHONEXSMAX欧美高级 ,
全职名医TXT免费下载 ,
剑域风云小说在线阅读 ,
心有不甘之苏寅正重生 ,
四合院知青下乡融合 ,
烽火战国官网手机版 ,
陈扬绝世高手最新免费全文 ,